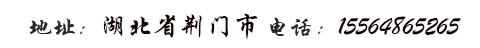生尘卅五middot贝母
|
网络编辑求职招聘QQ群 http://liangssw.com/bozhu/12719.html 书接前文,我们说到枇杷叶清金制木之功,此处有一味药值得与枇杷叶一较短长,这就是贝母。 王旭高在肝火证治下分列数条,与枇杷叶和贝母有关的两条分别是:“肝火上炎,清之不已,当制肝,乃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也,如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天冬、玉竹、石决明”;“景岳治郁怒伤肝,气逆动火,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证,用青皮、陈皮、丹皮、山栀、芍药、泽泻、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经之郁火也”。 前面谈过枇杷叶,现在我们来看贝母。 本图来自朱琦琦同学,摄自南京中医药大学药苑 《本经》以其味辛平,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 《别录》以其味苦微寒,疗腹中结实,心下满,洗洗恶风寒,目眩项直,咳嗽上气,止烦热渴,出汗,安五脏,利骨髓。 《伤寒》与《金匮》各有一处言及贝母:一为三物白散,治疗寒实结胸;一为当归贝母苦参丸,治疗治妊娠小便难。 从这四处较早的文献看来,化痰止咳在当时根本不是贝母的主流用途!反观所主诸症,如淋沥、疝瘕、乳难、腹中结实、心下满、结胸等,可见贝母几乎是以一味通利药的身份出现的,正如张山雷在评价川贝、浙贝优劣时就曾提到:“详绎《本经》、《别录》所主各证,皆惟象贝母之苦泄辛散,足以当之,非必川贝之淡泊而无味者,所可混同施治者也。” 此处需要留意的是,除了当归贝母苦参丸之外,历代方书中再也没见到贝母治淋的影子,文献断代也未可知,倒是程门雪先生曾用化肝煎治疗淋证因于肝郁化火者,姑作参考。 《大观本草》引陈承别说:“贝母能散心胸郁结之气,则《诗》所谓言采其虻者是也。盖作诗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之,今用治心中气不快、多愁郁者,殊有功,信矣。”(按:虻,或写作蝱、莔,此处均指贝母) 后世虽然多以贝母化痰止咳,但催生下乳诸方中用贝母者,亦取其通利之功: 《药性论》以贝母治虚热,主难产,兼治胞衣不出。 海藏祖方下乳三母散,用牡蛎、知母、贝母三物为细末,猪蹄汤调下。 傅青主立保产无忧散,用以临产催生。《医学心悟》引此方,解释颇为有趣。 再如比较小众的《产孕集》宣营汤,用温养之药益阳化阴的同时,加入贝母、红花、川芎以通利,治疗新产无乳。 诸如此类,本草方药相互印证,可见贝母确有开郁通利之效,这也是化肝煎中贝母清化肝经郁火的基础。肝者体阴用阳,郁怒伤肝,气逆动火,本就容易耗伤肝阴,而疏肝解郁之品性多香燥,这时有个凉润的贝母来开达肝郁,当真是无上佳品。 因此再细细回味肝火证治中的两条,同是清金制木(贝母单味药可算作清金制木之用,但化肝煎作为一个整体则不属于清金制木的范畴),枇杷叶因其善于下气,故着眼在一个“逆”字,贝母因其长于通利,故着眼在一个“郁”字。 另外,《西溪书屋夜话》以肝气、肝风、肝火三纲鼎立,程门雪先生百尺竿头,将肝火细分为实火、虚火、郁火三类,又将郁火治法分为两种,“首宜升散,次则横通,散肝者宣达升散之法,化肝者横通旁解之方”,虽未出治肝卅法范围,但说理晓畅,实于后学者多有裨益。 小钻风:为学日进,为道日损。 如果您觉得文章还有些许裨益,欢迎给作者小钻风打赏: 草木子平台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cane.com/ksjj/10664.html
- 上一篇文章: 金匮要略middot妇人妊娠病脉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