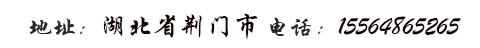医史新论良方与奇术元代丝绸之路上的
|
良方与奇术:元代丝绸之路上 的医药文化交流 罗彦慧 摘要:元代丝绸之路上的医药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各地的药物和医方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被中原医家接受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医药的进程。本文梳理元代丝绸之路上的医药贸易,研究中原医家对外来药物和医方的认识和使用,以及元代社会各群体对外来药物和医方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探讨元代丝绸之路的医药文化交流。 关键词:元代西域丝路医药 元代苏天爵所著《元文类》收录有王磐《太庙上梁文》一文,文中记载:“抛梁东,瀚海无波舟楫通,行见新罗兼日本,共来助祭贺新宫。抛梁西,西域重开路不迷,碧瑱明珠驮满背,香犀药草似长堤。抛梁南,楚风清脆尚虚谈,供祭包茅宜早贡,莫夸天险恃江潭。抛梁北,万勇不能当一德,龙沙战土涨天潢,舞干未久苗来格。”此记载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元朝疆域之辽阔,物产之丰富。辽阔的疆域极大方便了元朝与世界各地之间的沟通,也方便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有元一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畅通,各种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腹地,医药尤甚。元朝的医药体系比较多元化,陈高华认为:“元代为人治病的主要是中医,其次是回回医……大批蒙古人移居中原以后,每遇疾病仍求助于上天、巫觋,但请中医、回回医看病日趋普遍。”“回回医”在元代基本上是外来医药的总称,影响了元代的很多医药体系。元朝统治者本着实用的原则,接纳各种医药体系,世界各地的药物和医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并与以中原地区中医药体系为主的医药体系交流互动。 一、元代丝绸之路上的香料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和流通古已有之,至元代,伴随着元朝统治者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以及海上贸易的繁盛,香料的进口以及本土香料的种植都更为方便,香料的使用尤其是在医药学上的应用也逐渐使其从贵族阶层的奢华享受走向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得香料的身份逐渐平民化。元朝辽阔的疆域和统治阶级开放的态度,极大地方便了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和医药文化交流。有元一代,伴随各地奇异物产以多种方式传入,药物医方和奇药名草也随之传入。《至正集》卷三十一《大元本草序》记载:“开辟以来,幅员之广,莫若我朝。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岁虚。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万里,驷传往来,不异内地,非与前代虚名羁縻,而异方物产邈不可知者比。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朝廷为设官司之,广惠司是也。然则欲广《本草》以尽异方之产,莫若今日也。” 丝绸之路 《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代香料贸易的繁华和香料使用的普遍。“回回”是香料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回回”地面也是香料的重要产地,“回回”医师更是香药的主要使用者。元代丝绸之路医药交流的集大成之作《回回药方》残卷中的常用药物就包括从中亚、西亚传入的香药,有种之多。 《明史》 如东罗马的茴香(大茴香),喀布尔的诃梨勒,亚美尼亚的石头(大青石),印度的化食丹,犹太地面的膏子药,克尔曼的茴香,阿拉伯的橄榄油,索科特拉岛的芦荟,波斯的紫丁香、都龙知(吐根),土耳其的龙胆、朵梯牙(皓矶)、可铁刺(西黄耆胶)、猩猩毛发、红宝石,亚美尼亚产的红玄武土,埃及产的缟玛瑙、尼罗河柳的果实、松子仁、山香莱、西域芸香(漆树科乳香)、咱法兰(番红花)、阿飞勇(亚片)、李子树胶(三额、阿拉伯树胶),法尼的砂糖(锭子沙糖)、可落牙(产于亚美尼亚的莳萝,维吾尔族呼作孜然)、哈而八吉(藜芦)、海速木(洋蒿)、摩勒(余甘子)等。有些本是华化已久的胡药,如苏合香、荜芨、肉豆蔻、安息香、龙脑、胡椒、菖蒲、乳香、没药、腽肭脐、安石榴、血竭、阿月浑子、胡葱等。 元代的海上贸易极为繁盛。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一书记载了元代与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香料贸易。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西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荜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草原帝国》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描述了刺桐港的贸易盛况。《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ndrie)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税十分之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由此记载可见,在刺桐港贸易的货物中有大量香料,而且元朝政府对香料征收的赋税较其他货物来说更重。 元代的市舶司多为色目人掌管,色目商人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基本上掌控了元代的海外贸易。色目商人蒲寿庚及其家族为元代海外贸易的繁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蒲寿庚及其家族在宋代时就已掌管市舶司,宋元鼎革后,蒲寿庚继续掌管元之市舶司。在蒲氏家族的经营下,泉州成为最繁华的世界贸易港口之一。马可?波罗在行纪中说刺桐港(泉州)是“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几难信有其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也称,刺桐港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蒲氏家族将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至元代推向鼎盛。蒲氏家族之后,担任市舶司提举的还有沙的、马合谋、赡思丁、哈散、木八剌沙、倒剌沙、亦思马因、八都鲁丁、忽都鲁沙、暗都剌等十名色目人。另外,蒲氏家族的女婿、元初著名色目人巨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以上。可以说,色目人对元代的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香料则是元代海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 二、传入元朝的域外药物和医方 元政府对各地药物和医方采取欢迎和支持态度,故各地奇珍异物都源源不断地输入,不断地丰富中国医药的内容。 刘郁《西使记》记载:“(撒马尔罕)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疾甚效,曰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曰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傅疮上即出;曰奴哥撒儿,形似桔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碎傅之自续。余不能尽录。”《西使记》的记载生动而有趣,这些药物在治疗跌打损伤、金疮等外科疾病方面有奇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诸多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药物和医方。“火失剌把都”是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一味药物。《南村辍耕录》卷七《火失剌把都》记载:“火失剌把都,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马建春认为“火失剌把都”在元以前已传入中原,但当时中原医药界对其药性认识不足,至《南村辍耕录》成书时,中原医药界对它的认识已大为深入。明代《御制本草品汇精要》正式收载“火失剌把都”,称其为“苦只剌把都儿”,但“只列其名于目录,并无专条”。李时珍《本草纲目》将“火失剌把都”华化为“番木鳖”,详细记述了其性味主治,并附方四首。 “押不芦”是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一味麻醉药物。《南村辍耕录》记载:“草食押不芦,虽死元不死,未见涤肠人,先闻弃箦子者。漠北有名押不芦,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药解之即苏。华佗洗肠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周密《癸辛杂识》对“押不芦”的记载最为详细:“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佗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约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之卢松崖。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胡椒 “木乃伊”或“蜜人”是丝绸之路上流行的神奇药物之一。《南村辍耕录》记载:“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后,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回回药方》卷十二中载有“木蜜纳亦”一药,其注曰“即是蜜煎回回”,由米昔儿(埃及)输入。“蜜人”或者“木蜜纳亦”的出现,说明以蜜、糖做药剂、药引的回回医方已为中原医家所接受和采用。 《南村辍耕录》中还记载了一些“西域奇术”。《南村辍耕录》卷九“奇疾”记载:“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胁。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杨璃的《山居新语》记载:“哈剌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马则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顷复出一舌,亦剪之。又于其舌两侧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南村辍耕录》和《山居新语》都讲述了“也里可温人”广惠司卿聂只儿用“西域奇术”救治驸马奇疾的故事。 《南村辍耕录》之“西域奇术”还记载了“回回”医官为小儿开颅取小蟹之事,其记载为:“任子昭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迹遄止。尝求得蟹,至今藏之。”《波斯语汉语大词典》中Saratün有四种含义:癌,毒瘤;巨蟹星座;阿富汗阳历四月;螃蟹。宋岘认为:“在阿拉伯语中,蟹被呼作Saratün,即《回回药方》所言之’撒剌唐’,在此转义为癌、毒瘤。‘取一小蟹’,实是回回医官为小孩做了次切除癌肿的小手术。(唐)杜环《经行记》言,大秦国‘开脑取虫’,其医术与此雷同。”《南村辍耕录》之“西域奇术”还记载了“老回回”从马腿中取出“小块”的故事,其记载为:“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闾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观之,于左腿内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即骑而去。信哉西域多奇术。” 元代王沂的《伊滨集》卷五《老胡卖药歌》生动描绘了西域人行医卖药的情景。“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居人相见眼终青,不似当时答术丁。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烦说《难经》。江南只今成乐土,异代繁华复亲睹。全家妻子得安全,箧里青蚨夜还数。灯前酌酒醉婆娑,痼疾疲癃易得瘥。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来人极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文效如昨。眼中万事不足论,流寓无如胡贾乐。”由王沂的描绘可知这位行医卖药的“老胡”医术不凡,为世人称道。 元代丝绸之路上医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之作《回回药方》中记载了许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药物。据学者统计,《回回药方》中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香药有种之多,比如八剌班油等皆出自遥远的“蜜斯儿(埃及)地面”。《回回药方》对香药的使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回回药方》中很多方剂以香药命名,如乳香饼子、白檀饮子、檀香膏、沉香膏子、荜澄茄汤等。有的方剂中甚至全部使用了芳香药,如麝香膏子就是由麝香、肉豆蔻、草果、丁香、胡椒、荜芨、沉香、官桂、丁皮、良姜等芳香药物组成。这些香药多来自域外和少数民族地区。 《回回药方》 元代丝绸之路上饮食文化交流的集大成之作《饮膳正要》中的很多食材来自域外及少数民族地区,而其中记载的食物和饮料多有养生价值,与药膳类似。《饮膳正要》卷三《料物性味》中记载的胡椒、莳萝、草果、荜拔、缩砂、荜澄茄、苦豆、胭脂、稳展、哈昔泥、黑子儿、芫荽子等皆产自域外或者少数民族地区,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成为烹调佐料或者药物。《料物性味》中还记载了一些来自“回回地面”的佐料的药用价值,如“马思答吉,味苦香,无毒,去邪恶气,温中利膈,顺气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生回回地面,云是极香种类……咱夫兰,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敷热毒疮肿”。 《饮膳正要》中记载了许多使用香料为佐料调制饮食的方法,如用阿魏树根腌制羊肉的菜肴:“稳展:味辛,温,苦,无毒。主杀虫去臭,其味与阿魏同,又云,即阿魏树根,腌羊肉,香味甚美。”《饮膳正要》中还有用玫瑰水、咱夫兰等烤制羊肉的菜肴,如卷一《聚珍异馔》记载:“炙羊心:治心气惊悸、郁结不乐。羊心一个,带系桶,咱夫兰三钱。右件用玫瑰水一盏,浸取汁,入盐少许,签子签羊心,于火上炙,将咱夫兰徐徐涂之,汁尽为度。食之,安宁心气,令人多喜。”另外,《饮膳正要》中所有羊肉类食物的制作几乎都用到了“草果”和“回回豆子”。 《饮膳正要》 元代宫廷饮品大量使用香料,《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中就记载了多种饮料,且大多添加香料,如荔枝膏、梅子丸中使用了麝香;桂沉浆中使用了沉香。《诸般汤煎》记载的饮品有桂沉浆、桂浆、人参汤、五味子汤、孩儿茶、枸杞茶、仙术汤、紫笋雀舌茶、女须儿、温桑茶、橘皮醒醒汤、杏霜汤等。这些饮品多添加香料、果品、砂糖等,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且口感佳美,这其中许多香料和砂糖都属于外来物品。 元代医家沙图穆苏撰写的《瑞竹堂经验方》中也有明显的丝绸之路医药文化交流的痕迹,书中记载的一些方剂名明确标有“海上方”字样。例如,“海上方,治恶疮:燕窝内外泥粪,俱研极细,罗过,用油调敷”;“海上方,治疔疮:蝉壳(七个,煅,为末),右为极细末,用蜜调,搽疮口”。“海上方”之字眼说明这些药方来自海外,是中外医药交流的成果,且以蜜为药引也非中医药之传统。另外,《瑞竹堂经验方》中收录了多个眼科经验方,与《本草纲目》中收录的三个来自“回回”地面的眼科方有相似之处。 《瑞竹堂经验方》中出现了大量直接以香药命名的药方,其组方中的主要药物都是香药,如“沉麝香茸丸”的组方中有沉香、麝香、南木香、乳香、八角茴香、小茴香等;“安息香丸”的组方中有延胡索、茴香、木香、真阿魏、真安息香、麝香、没药;“丁香烂饭丸”中有丁香、木香、缩砂仁、香附子等。以上只是《瑞竹堂经验方》中一小部分直接以香药命名的方子。据笔者阅读并粗略统计,《瑞竹堂经验方》中直接以香药命名的方子不少于30个,而且此书2/3的药方中都有香药。从香药的使用角度来看,《瑞竹堂经验方》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医药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以上研究可知,《瑞竹堂经验方》是一部丝绸之路医药经验交流的成果,并非某一民族的医学体系。 《瑞竹堂经验方》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元代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内容丰富、庞杂,书中记载的很多医药和饮食都与丝绸之路的医药饮食文化交流有关。该书庚集《饮食类》中记述了12种“回回”食品的名称及制作方法,分别是秃秃麻失、河西肺、卷煎饼、糕糜、酸汤、设克儿匹刺、八耳搭、哈耳尾、古剌赤、海螺厮、即你匹牙、哈里撒。《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一书出现了大量与香药有关的记载,如出现专门的“法制香药”条,记载了九种香药的制法,分别是法制杏仁、酥杏仁法、法制缩砂、木香煎、法制桔皮、法制半夏、醉乡宝屑、法制虾米、法制木瓜。除了专门的“法制香药”条,该书所记载的一些经验方也大量使用了香药。另外,书中记载的一些汤饮、茶品、食物中大都使用香料,体现了香料在元代医药和饮食中的使用特点。 三、元代社会各群体对域外药物和医方的态度 大量西域药物的输入及其独特的疗效,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医学界对这些疗效显著的西域药物趋之若鹫,很多史籍对此有记载。许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称:“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许有壬的记载说明西域药物在元代医学界备受青睐且有着良好的声誉。亚美尼亚人海顿的《契丹国记》称,由波斯输入的橄榄油等被蒙古人"皆以重价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忽必烈十分重视西域药物,曾下令召天下名医增广《本草》,《元史》记载:“癸酉,命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 忽必烈时期,西域药物在中土已广泛使用,不仅西域人掌握这些药物,中土人士也识得这些西域药物。据苏天爵《滋溪文稿》记载,当时名医韩麒就能很好地辨认这些西域药物。苏天爵《滋溪文稿》之《医院使韩公行状》记载:“至元己丑,故礼部尚书许公国祯举名医若干人以闻,公与焉。帝召见便殿,各询其人所能,出示西域异药,使辨其为何药也。公食其味,独前对曰:‘此与中国某药侔。’帝加赏异,命为尚医。是时帝春秋高,体常不平,典领方药,蒙赐貂裘、玉带。辛卯,敕授医正郎、御药局副使。”韩麒因能辨识西域药物而被元帝授予“御药局副使”,后又授予“太医院副使”和“太医院大使”。一方面可见当时中原医生已能辨认西域药物,另一方面也见元政府对西域药物的重视,二者皆说明元代西域药物在中原的盛行。 元朝不仅将西域药物补入医典,还专门设立了掌管西域药物和医方的医药机构。《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记载,元政府特设广惠司执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而广惠司很长一段时间的掌管者则是西域弗林人爱薛。《元史?爱薛传》记载:“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马建春认为广惠司的设立,“突出反映了元代与西域医药的密切交流。像广惠司这样由域外人士组成并专门执掌异域医药事宜的机构,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此一例”。 广惠司所需药物除了大量从西域各地购进,西域汗国的入贡也占重要部分。《元史》多处记载了从西域购买和各国进贡药物的事实。《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记载,延祐七年(),朝廷旨令:“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二年(),“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物,赐钞千三百余锭”。《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记载,至顺二年(),“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元史》卷三十七《宁宗本纪》记载,宁宗时,“诸王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赐钞三千三百锭”。此处的“塔里牙”即“打里牙”。 泉州港油画 除了广惠司,回回药物院是元代在中央设置的又一重要医药机构,管理回人医药相关事务。《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在大都、上都始置“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至元二十九年始置。至治二年,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爱薛也是回回药物院的管理者之一。 元代除了官方设立的管理西域医药的机构,民间还有域外人士及医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周游世界的游记中记载:“余寓埃及人鄂拖曼后裔家中。鄂拖曼乃大商家,甚喜汉沙城,故常寓此。城亦由彼而得名曰阿尔鄂拖曼尼雅(Othmaniya),其子孙在此亦甚受人尊敬,善继父志,救济穷人。有贫僧来门求助者,彼赠之甚丰。医院(玉尔本作僧庵)亦名鄂拖曼尼雅(AlOtamaniya),建筑颇为华丽。此外各种慈善之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医院者甚众。鄂拖曼在此城尝造一回教大礼拜寺,名曰甲玛玛思及特(JamaMasjid)。并捐钱甚多,作维持费。回教徒在此者亦夥。”马金鹏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与张星娘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对此事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游记中的“尼雅”为疗养院之意,而“鄂拖曼尼雅”是带有公益性质的私人疗养院。元代应该还有一些民间回人医药机构,“鄂拖曼尼雅”因为《伊本?白图泰游记》而知名。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祭祀物品增加了许多外来物品。《元史》卷七十四《祭祀》记载:“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荐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鱼、馒头、T其子、西域汤饼、圜米粥、砂糖饭羹,每月用以配荐。”由此可见,在元代祭祀用的“牲斋庶品”中,新增的“西域汤饼、圜米粥、砂糖饭羹”皆是从西域及中亚、西亚地区所来。“祭器”中的香器也不在少数,如“香案”“香鼎”“香奁”等。 结语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极大地方便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医药文化交流,各地奇药名草和医疗方法以多种方式传入中原。有元一代,丝绸之路上的医药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元代各种文献中有许多相关记载。经丝绸之路输入的药物和医疗方式受到了元朝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大量药物和医方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原,对元代社会影响颇大。马建春称:“古代西域和中国密切的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药物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些药物的输入丰富了中国药物学内容,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药物被中医药界吸纳,编入各类医药典籍,成为中国药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大量域外和西域药物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不但丰富了中药的内容,扩大了中医的治疗范围,而且部分改变了中药的剂型。宋元时期中医走向详细的分科,中药也由单一汤剂为主的剂型,逐渐向丸散膏丹酊剂扩展。但是,由于香药大量入华和中原医界对香药的接受程度提高,宋元医界也出现了滥用香药的弊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明确反对《太惠民和剂局方》滥用香药。在朱丹溪等医家的理性反思下,医界对香药的使用也渐趋理性。除了对中医药体系的影响,元代丝绸之路上流传的医药体系对中国民族医药体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如藏医、蒙医以及西域诸民族的医药体系都受到了元代外来医药的影响。至明代,域外药物和医方多完成了其华化的过程,与本土医药融为一体。 [作者罗彦慧,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副教授] 转载声明 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第九辑(年6月),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编辑:张天卫责编:陆丹妮李津萍 编审:张勇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ucane.com/ksxz/8532.html
- 上一篇文章: 临床中药用药技巧秘传
- 下一篇文章: 12副中药方